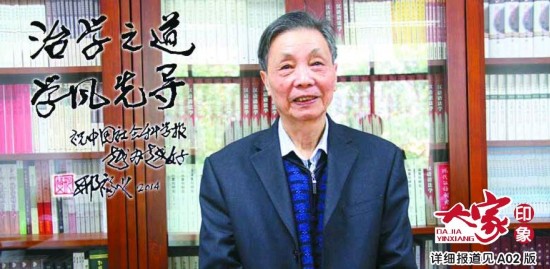
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,也沒有傲人的教育經(jīng)歷,華中師范大學(xué)文科資深教授邢福義憑著堅(jiān)忍不拔和勤思好問,在語言學(xué)界建立起自己的“學(xué)術(shù)根據(jù)地”。回顧50余年的治學(xué)生涯,邢福義語重心長(zhǎng)地說,中國(guó)語言研究只有植根民族土壤,方能枝繁葉茂。
如今,已步入耄耋之年的邢福義仍沒有停止攀爬學(xué)術(shù)高峰的腳步。2011年,由他擔(dān)任首席專家的國(guó)家社科基金重大項(xiàng)目“全球華語語法研究”立項(xiàng),這項(xiàng)研究旨在考察全球范圍內(nèi)華語的使用情況。邢福義說,身為一名學(xué)者,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不斷超越自我;而作為一名教師,他希望能成為學(xué)術(shù)團(tuán)隊(duì)的“引路人”,幫助年輕一代走得更遠(yuǎn)。
研究道路自己走路 走自己的路
談起師承,邢福義略帶詼諧地說,他在學(xué)校讀書的時(shí)間只有十年,其中小學(xué)和初中各三年,專師和大學(xué)各兩年。至今,他戶口簿上最高學(xué)歷一欄,填的還是大專。“我的學(xué)術(shù)成長(zhǎng)用‘自己走路,走自己的路’來概括比較貼切。”邢福義告訴記者。
一次偶然的閱讀,讓邢福義對(duì)漢語語法規(guī)律產(chǎn)生了濃厚興趣。正是憑借這份興趣,他最終走上了漢語語言學(xué)的研究道路。不過,當(dāng)時(shí)年僅21歲的邢福義面臨“先天不足”的窘境,因?yàn)闊o論在專師還是大學(xué)求學(xué)期間,他都未接受過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的系統(tǒng)教育。
這種“先天不足”并沒有成為邢福義的羈絆,反而促使他養(yǎng)成了向?qū)W問家學(xué)習(xí)的習(xí)慣。創(chuàng)刊于1952年的《中國(guó)語文》成為邢福義“自己走路”的起點(diǎn)。自1956年參加工作開始,《中國(guó)語文》上每發(fā)表一篇重要語法論文,邢福義都會(huì)仔細(xì)閱讀。他不但要求自己讀懂文章所闡述的論點(diǎn),還要認(rèn)真揣摩字里行間隱藏的“奧秘”。譬如,作者是怎樣抓到這個(gè)題目的?在研究方法上有何長(zhǎng)處?久而久之,他練就了捕捉論題的敏銳感,摸索出了適合自己的研究方法。
在邢福義看來,學(xué)術(shù)研究除了要“自己走路”外,更需“走自己的路”,明確個(gè)人特長(zhǎng)和優(yōu)勢(shì)領(lǐng)域,在建立“學(xué)術(shù)根據(jù)地”上下功夫。經(jīng)過多年積累,邢福義開始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創(chuàng)性的學(xué)說,如“兩個(gè)三角”理論、“主觀視點(diǎn)說”、“句管控”等。這些富于創(chuàng)造性的語法思想不僅為他在學(xué)界贏得了聲譽(yù),也成為他“走自己的路”的最好注解。
研究理念研究植根于泥土 理論生發(fā)于事實(shí)
相較于學(xué)術(shù)成果,邢福義更看重學(xué)術(shù)追求。“研究植根于漢語泥土,理論生發(fā)于漢語事實(shí)”是他始終堅(jiān)守的研究理念。“小句中樞說”就是一個(gè)很好的例證。
“如果孤立地看漢語的七種語法實(shí)體,不管是語素、詞、短語,還是小句、復(fù)句、句群和句子語氣,沒有哪一種不可以成為語法研究的重點(diǎn)。然而,通過對(duì)漢語語法事實(shí)的全面觀測(cè),我發(fā)現(xiàn),在漢語語法機(jī)制的形成和運(yùn)轉(zhuǎn)中,居于中樞地位的是小句。它能夠控制和約束其他所有語法實(shí)體,起到‘聯(lián)絡(luò)中心’和‘運(yùn)轉(zhuǎn)軸心’的作用。”邢福義說:“這個(gè)理論提出之后,曾有學(xué)者認(rèn)為,無論是從研究方法還是從語法體系的本質(zhì)來講,它是一個(gè)按照漢語的面貌建立起來的語法理論。這種評(píng)價(jià)讓我很欣慰。”
在邢福義看來,真正適合我國(guó)語言文字的理論,最終只能產(chǎn)生于我國(guó)語言文字事實(shí)的“沃土”之上。國(guó)外理論的引進(jìn)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,經(jīng)過演繹轉(zhuǎn)化,在我國(guó)的漢語事實(shí)中“定根發(fā)芽”,最終形成適合于中國(guó)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。
他十分期待,有朝一日,中國(guó)語言學(xué)研究能夠形成“中國(guó)學(xué)派”,以鮮明的民族性,為國(guó)際學(xué)界慷慨奉上“中國(guó)特色”的思想精髓。
治學(xué)原則畢生倡導(dǎo)“樸學(xué)精神”
1993年,在慶祝呂叔湘先生九十華誕之際,邢福義專門寫了一篇題為《治學(xué)之道 學(xué)風(fēng)先導(dǎo)》的文章,借此表達(dá)他對(duì)呂先生“務(wù)實(shí)”學(xué)風(fēng)的敬佩。“樸學(xué)精神”也成為他畢生的治學(xué)原則。
邢福義說,“樸學(xué)精神”就是要質(zhì)樸、實(shí)在,講實(shí)據(jù)、求實(shí)證。他經(jīng)常把“看得懂、信得過、用的上”的“文章九字訣”掛在嘴邊。他向記者解釋說,寫文章首先要讓別人看得懂,然后要讓別人相信結(jié)論的可靠性,最后還能運(yùn)用到實(shí)踐中去。具體到撰寫現(xiàn)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文章,一定要講求實(shí)據(jù),通俗易懂,并考慮國(guó)內(nèi)語法教學(xué)、對(duì)外漢語教學(xué)以及計(jì)算機(jī)信息處理等實(shí)踐應(yīng)用。邢福義特別提到,面對(duì)當(dāng)前語言學(xué)的跨學(xué)科發(fā)展趨勢(shì),在運(yùn)用新的理論方法和科技手段時(shí),一定要反復(fù)論證,據(jù)實(shí)思辨,不能醉心摩登,急于求成。